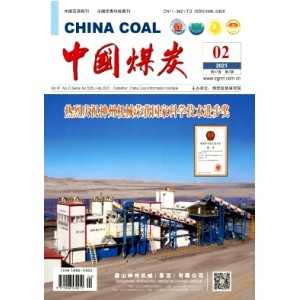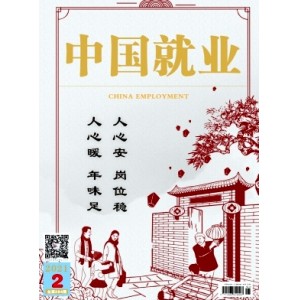民族艺术杂志在线阅读
“叛师”与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
——历史人类学的探索与反思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2568(2019)06-0005-07 中图分类号:C958.8
----文章选自民族艺术杂志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以来,作为方法与视角的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学界一直是一种多面的存在。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与人类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体系、研究力去与表述系统上差别甚大。这既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常态分野,也是不同学者之研究旨趣上的差别。因此,当我进入这个知识领域之时,不仅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学习环境对自己的思维取向做定立,还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构成了我十余年来学习与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一、在承袭中探索:师公的仪式、神灵与文本2005年,就读历史教育专业的我原本计划毕业后去当中学老师,但经历了大四第一个学期的实习之后,觉得中学历史教学中较强调标准化而
非个性表达的环境并不太适合自己的个性,于是经过一番挣扎,在实习结束后报考了母校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人学后的第一个月,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黄振南教授找我谈话,问及学业规划并给我指出了未来的方向:我必须攻读博士学位才有出路。他的基本意见是,我如果想在高校中谋求一个教学科研职位,最起码必须获得博士学位。对此,我虽然尚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也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学术生涯历程。
黄老师是国内中法战争研究知名学者、为了兼顾我的专业方向和他的研究领域,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做毕业论文,他让我做中法战争后边防建设对桂西南地区壮族社会历史的影响这一选题。
我按照他的指导去搜集史料,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区域的材料更具体,针对壮族等民族的材料则很少。于是,我当时萌生出一种突破单个民族史研究框架、结合区域与人群进行研究的朴素想法,但自己在这方面毫无基础,只好跑到图书馆去找相关的书籍。
当时,处于学术启蒙期的我,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下卷),抱着翻翻看的态度拿来阅读。这本书是2001年他们召开的一个纪念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百年的大型学术会议论文集。
我在书中看到了赵世瑜、刘志伟、陈春声等老师的文章,觉得挺有思想刺激。意犹未尽之余,我借了赵世瑜老师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一书回来读。虽然彼时只是雾里看花、观山思海,但在赵老师细致的学术梳理中感受到了区域史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往后的阅读与学习过程中,我喜欢模仿杨念群、王铭铭等人的笔触撰写必修课的课程作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两篇习作竟然被时任(广西民族研究)主确的平乃昌老师看中,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上、"后束,我将提交给罩圣敏老师的课程作业投到《世界民族),居然也被刊用。“现在观之,这些文章只是识读路上的片想,但对于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文章能够在核心刊物发表,确实令自己信心倍增,无形中增强了走学术研究道路的念想。
在习作发表之余、硕土求学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08年参加第六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经历。这个高级研修班自2003年由赵世瑜老师作为核心策划人由萧凤霞老师出资在北京师范大学首次召开,此后由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院校连续合办,迄今一共举办了13届。研修班旨在通过课堂讲授与田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年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
研修班的第一个阶段是理论授课,我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聆听了萧凤霞、滨下武志、刘宏、文志伟、郑振满、陈春声、赵世瑜、程美宝、张佩、刘永华、温春来等诸位老师的精彩演讲。随后我们分为几个组,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各位老师的带领下,从广州前往福建龙岩平和县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我们白天跑田野,晚上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文献阅读与讨论,直到如今,温春来老师和吴滔老师带我们阅读文献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无论是在中山大学永芳堂的授课,还是到福建平和县的田野考察,都让我迷上了这种知识工作方式。尽管彼时我对老师们解读族谱、碑刻、契约和地方志的方式与田野调查的真正意义认识尚浅,但是他们做田野的方式、看材料的想象力和讨论问题时的严肃,让我感觉到了他们身上散发出
的深厚学术魅力。因此,后来决定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专业,不仅是一种学习兴趣,更是一种学术情怀的感召使然。
2009年9月,承蒙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不弃,我得以拜入门下攻读历史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人学之后,基于此前的阅读,我徜祥于帝国土司、边界等标签,很想延续硕土论文关于中越边境地区的讨论,做桂西南的土司研究。正当我准备开展阅读计划之时,却发现这个研究方向与杜树海师兄选题有较大重复。出于大家学术发展差异性的考虑,我决定换题。当时考虑最多的方向就两个:一是题目有点意思,自己也感兴趣的;二是三年内有可能按时完成的。于是,我在有限的阅读经验里追寻自己能做也想做的选题,最终,我把广西师公视为一个可能完成的研究对象
我的父亲是一名师公,我身为一个“文化持有者",尽管自小便接触师公的各种仪式,但却对师公及其仪式多处于一种“日见而不知"的状态。在确定选题并开展初步的田野调查与文献阅读之后,我兴致勃勃地向老师们汇报广西师公的基本情况时,不假思索就用了先行研究者的概念,将他们说成"师公教”。科大卫老师和刘志伟老师听了我的汇报,都同时间一个问题:你所说的到底是“师公教”还是"师公”?我当时的回答自然模棱两可,尚未明白两者有何本质区别。老师们就此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让我明白,若想研究师公,必须首先清楚他们的自我理解与称呼是什么,而非前人研究给他们贴的标签。关于师公的称呼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对于推崇从当地人视角来理解补仪标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而言,却是我的博士论文建立解释框架的根本性认知基础。由此我逐渐明白,我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弄清楚仪式专家的自我认识及其仪式传统的核心内容。
结 语
行文至此,我深知在学术成长初期谈论“叛师”与自我管理等问题,定会被很多人所不齿,毕竟我们目前依旧在老师们探索出来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上开展具体研究,遑论开辟新的领域。
但我愿意相信,我们所处的时代,研究对象、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和学术对话的对象都与师辈面临的状况大有不同,会因时、因势发生转移。这种转移既是对老师的一种悄然的、不自觉的“反叛”,同时也是将原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拓展到新领域的过程。所幸,从事华南研究的老师们都是极具学术包容心的学者,他们深知自己历经几十年承继前辈学人开拓出来的学术志业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持续加入才能有更多洞见,因此,他们向来都是鼓励我们大胆去寻找新的研究问题。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精微审慎及他们所构筑的学术共同体内部间严肃、纯粹的相互批判传统,是我今后学术生涯永远的精神明灯。
本文章从互联网采集,文章摘自于民族艺术订阅,文章版权归民族艺术杂志和作者所有;仅供需要民族艺术订阅的朋友试读,请勿用做它途;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24小时内删除,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