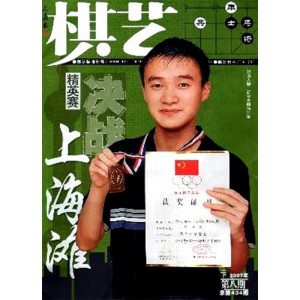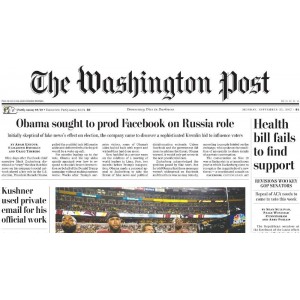同类书刊排行榜
- 畅销榜
- 收藏榜
-
时代周刊time马斯克封面单期(1本现货)3天内发货
-
首席财务官
-
徽商
-
商业文化
-
全球商业经典订阅(停刊)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中国外资
-
商业评论
-
棋艺杂志
建筑创作杂志在线阅读
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时空联系”与公众参与体系
Time-Space Connections and Participation System
in Public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文章选自建筑创作杂志
要访者:齐欣,《人民日辰》(海外版)高委编辑,195年至今长肌从事文物保护。文化通产及相关领域的报道。研究方商为文化通产传播与公众参与体系。
票访时间:2018年7月17日
AC:本次方豪程集新面向公众证镇方案之外,还调动社会力量对场地进行为用 24 小时的观察,形成视察报告。既是为设计者提供真实的问题和素材,也能让距家公众有机会深入了降胡同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从传播角度来着,您认为以方案征集为介质的公众参与模式的价值和局限在哪里?
齐欣:如果将方案征集本身扭为一个公众参与的案例,我们可以同时从传潘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观察个体、群体和团体彼此如何相互影响。在文化遗产传指实践中,类似于方案征集的 24×20 观家计划是经常发生的案例。我强烈支持并希望这种我们称之为“公共文化产品”的案例能够长期多点、反魔进行观赛和记录。例如,我坚持记录上班途经的大望路,渐渐从“人的聚落”的角度来看待它——大望路—侧是 CBD,另—侧是长途汽车站,北京东站这些原本应处于城区外围的功能区。如果我们将观察的内容都作为“信息”,比如看到的事件、听到的声音、当时记录的自己的感受……然后,希它们放在“时间轴”上,这就具有了社会学和人类学样本意义。甚至,只要再有意识地加上一点点记录工具的要求,那这些公众参与模式,就同时具有了文化遗严传播所渴望的 GIS(地理信息系统)“库数据”的意义。
如果说到局限。第一就是目前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参与衍生出的“公共文化产品”价值及其与“商业文化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导致了许多的参与更像是一种“表演”,截止到“宣传”的目标就止步不前了。从传播的效果来看,我们非常关注西城区的案例,能够持续地提供有意义的结果。第二,公众持续的参与一定会让参与者追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将归结到社会对于公众力量的定位,或者参与者的“获得”与“回报”。目前,公共政策体系非常缺少一个活跃的、有意义的遗产地实践结果,来诠释这种定位或者“回报”——西城区代表的“中轴线西侧”遗产区,非常有研究价值。
AC:您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传播工作,曾提到自己的生活由三部分组成:行走、写作和讲课。您的身份也在媒体人、教育者和研究者之间切换,它们在文化退产传播的工作中如何协调?
齐欧:新闻工作的本质,是观察和使用信息的流动。这是个“技术活儿”,需要长期的职业能力培训。所以从传播的视角解释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过程,也就可以描述为信息的逐步趋同过程。文物部门将文化遗产语境中的“人”分为三个主要类型,访问者(游客)、居住者(居民)、管理者(管理人员、专业人士)。至少,从中文语境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实践来看,这种划分方法过于简单或者说“过时”了。这是按生活时段来划分,还是按照交通方式——比如步行或骑行——去划分?现在受众自我身份认同的方法与界限已经被打破重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他的身份可以在访问、属住和管理研究中频繁而自然地转换。我在西城区出生;大量工作是骑车在大运河!沿线勘察;每天从家出门,至少两次穿越大运河边。我介绍自己时,却很少说自己是“原住民”,那么到了外地的河边,我是算“访问者”、“居住者”还是“专业人士”呢?
所以,文化遗产传播实践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认同和辨识的原动力。和大多数文化遗产公益传播者一样,我认为我们还是原来的“我”——我终究是个记者。但是,我开始懂得利用信息传播的流程,发挥别人没有的“看信息的专业技能,去推动文化遗产价值的正向传播。于是,行走、写作、讲授,都是同一个流程上的不同位置。我只是做了传播者应该做的。
西城区现在的居民很多并非“本地人”,那么这种 24×20 观察计划是不是偏离了遗产地“原住民”?我觉得这种“偏离”恰恰是好事。文化遗产传播首先要认同变化中的价值演化,但这种演化与真实的存在价值和延续价值是有逻辑关系的。在这个基础上,文化遗产传播并不一定只培养本土忆旧的感觉,不一定刻意关注“老”和“旧”,老旧不等同于有价值。我们的调查发现:如果只是忆旧,容易将本地居民和游客区分开,外地人就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从潜在的责任中剥庵出来,而无法自发产生共鸣——“这是你们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的印证。所以,关注文化遗产价值和遗产地精神的体验与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文语境下面临的巨大难题。
AC:传播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主要处理哪些工作?通过您完成的实践经验总结,您认为文化遗产传播需要注意些什么?
齐欣:我刚刚体验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一个研究课题,于冰老师在淮阴师范学院带领学生进行了促进大运河沿线居民认知水平的大学生暑期实践。在实践中和村民沟通,我发现多数村民仍认为文化遗产与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这就是价值和人的需求没有相互协调,文化遗产传播的工作没有到位。文化遗产传播在宏观层面要扎实地把握以下几个节点
1.关注“名”的增减。“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名村”、“名街”与遗产地的重合关系越来越明显。”名”是一个传播结果,而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和客体既可以越来越有名,也可以越来越无名,重要的是“名”的真实性是如何保证的?以及怎样在和规划专业的合作中保证“名”的有效性。
2.文化遗产价值信息的“扁平‘和“下沉”。所谓“扁平”,是指信息被受众寻找和接受时,所经历的环节是否简单通畅,也就是说不要太费劲就能找得到;“下沉”则是指文化遗产价值理念在遗产地民众中曾及程度和被接受程度。文化遗产理念的传播,要经历从精英理念向社会大众的逐步曾及和扩展的过程。这其中位于“人的聚落”最末端和前端的基层单位,其价值趋同目标面临着全方位挑战。我们花时间调研不同层级的“利益相关者”如何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就会发现拆迁矛盾多是生活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一个普遍问题,深层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传播需要解决价值目标在更大范围内的支持和协同。
3.既要关注“物”,也要关注“人”。许多人对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除了关注物质遗产,也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技艺的载体是“人”。这只是答对了一半。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信息记录者和价值阐释者,既要能够描述作为文化遗产的现价值对应物,也要关注在文化遗产不同发展阶段人的想法,以及如何在现实中,印证这些想法产生的结果。
AC: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地囊括非物质文化对象,文化遗产传播的观念与方法需要进行哪些调整?与规划专业如何配合?
齐欣:价值、价值的阐释,都有其时空范围。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将传播的“时空”,规划的“时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时空”,地理信息领域的 GIS“时空”相互连接,并且找到一个平台去应用起来。选糯决。低厚。从各个领减上看。“大遗址”、“风粮区”的保护越来越普遍和具体,这个时刻,文化遗产传播就大有用处了。护时代。或馨说,该奈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和文化源产理念还没有扩展到足够“大”的范围时,保护对象常常都可以用“点状”而非“面状”的方端”定义来者。这个效据的评性非常容易高化。那就是“流量统计”和“经济效益”两种方法。但是,文化遗产传播说到底是一种社会事业。在文物保
文晚流产悻情着一个无生的特点,它处理的是专业认知向大众哩解、精英共识向社会认同的转调,并通过方法产生相应的效果。如果从“宣传”和“营20哈年7月,“平国地海高是产业年余”在海口举行。这次大会,破天荒地举办了一个金新的论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就去诺的题后亳《文境通产传播中的G5应跨蹇求——-以大运河遗产小道体验线踏为例》叫。后来陆续接触到了一些听众的反馈,给我震动很大。娛来满,这个年会是车常专业化的技木人员扎烷的内部聚会,但是她们却对我所描述的在“遗产小道”上拿着手机去找路体验的“人”给迷住了。我这么格一点都不过分:文化者产价值简释需曼体验的“时空”,也就是说你不能泛泛一指“这都算,去看吧”,也要非常具体地告诉体验者从哪里开始,在哪查得圈。尤其是高里可以不去不用走冤枉塔。那这个速产价值的“时空”和地理信息的“时空”是如何对接的呢?我们还在探索。
2007年,西城区开始推出旨在提升街道公共空间品质的《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规划部门创造性地将“遗产小道”方法和路线,引入了《导間》中,这些对是一次全新的、前沿性的实践。因为规划界和传播界的思踏大相径庭,传播者的工作是让受众体验文化遗产价值和遗产地精神。设计“小道”常常要怎么走都成,只要符合“位于遗产区范围、不破坏风貌、步行或者骑行”。但是这条线路在规划师的设计要素中常常是不存在药。比如人的停副点和观看点的设计缺失。
《导则》与“遗声小道”的这个例子,可以说上很久,对其它城市或者“人的聚落”,也有实践意义。这意味着规划部门开始由对政府负责,逐步舞向以“人的硬得与感受是求”这个更大的范围为规划目标。文化遗产传播也要适应这种结合和转变,更加着眼于强调文化遗产传播的“公共性”,以反在处其文化产品和原业文化产显之间。导找合适的比例。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公共文化产品作为基础力量,所有简单使用文化遗产价值的商业文创,成吃幸都不会高。因为它们恰恰没有把受众作为“主语”,而是简单地把“文化遗产”直接做了主题,这样反而就太不公共、太小众了。目前地理信需要的是有一点长远的眼光,再加上一点点耐心。
传播。电子地图这些原來各自为政的局面,会很快融合起来。文化遗产理念带来的影响是多元而具体的,产生的回报和模式也是巨大而不可逆的。现在息平台过于技术化,目主要面向政府、企业等专业用户,体验受众很难在电子地图上规划出体验路线及其延伸产品。由于行业长远目标的一致性,规划、奔校: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社会参与吗?我更愿意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来阐释。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自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AC:文化退产保护领域的参与方正在由专业保护机构转变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体系,是什么促使了转变的发生?
公约(巴黎公约)”出现算起,文化遗产理念用了将近 50 年的历程,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各个国家、民族和普通人群的共识。这个过程分为了宣展、对冲、接受、一致等社会交互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文化遗产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理念的传播。
这种传播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做是由小众的、外部的、精英的理念逐步地全球化,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下沉”,在中国,从1985年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加入“巴黎公约”后,文化遗产理念逐步被各界所接受,至今已成为导引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仅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上升,影响力增强,遗产保护的面积范围也大大扩展。在这些扩展的范围里是有人居住生活的,如此一来,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就明显无法由文物部门一个专业部门来承担了。
从传播的对象来看,文化遗产理念在中文语境下,也开始更广泛、更基层地对各种“人的聚落”产生影响。比如,原来只有“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就有了“名村”和“名街”。从传播的角度,理念的正向流动趋势正在向基层“下沉”。“下沉”是好事,但也同样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是天然的支持者。
2016 年,我们在北京市西城区做了《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城区:中轴线西侧——北京西城区“四名””体系的功能和演变》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西城区的大多数街区管理机构处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远端”和“冲突的尖端”。社会各界价值多元,导致了传播者和受众——同时又是遗产地中的“利益相关者”——形成价值观统一的过程漫长。这就非常需要从法律、法规的高度去看待、肯定和规划这种“多元价值对冲和趋同”。也就是说,社会力量参与,最终而且越快越好地,要形成有效的公共体系。
于此同时,专业保护圈内也需要出现更多人,承担“传播”的功能,而且还要更进一步由业知识宣传者,变为社会影响力的供给者。如果回忆那些我们至今仰望和怀念的文物保护前辈,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成就突出,更有意识地呵护着一种无形的合作平台。从梁思成先生开始,前辈们的专业认同感和社会使命感都很强。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交流还“互相通气”。他们那个时代,规划建筑界、文物保护界存在着真挚的、互通的合作渠道。我亲身经历了与罗哲文、郑孝燮等老先生一起工作的时光。你会发现在他们人生生涯后期,几乎都不再做本专业的具体项目了,更多是以“游说”活跃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老一辈的人可能不懂传播专业,可是他们懂得怎样将人的力量聚在一起——文化遗产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游说者”。当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侯仁之”、“罗哲文”?我认为是缺乏有眼光又兼具勇气的行业专家,去聚集、融合社会力量。
但是,必须看到,当初老一辈人达到这种“聚集”并非靠“公共体系”,而是依靠自己多上通下达的位置。当文化遗产由一个点扩大为“区”和“城”这些更大范围的概念时,就不能仅仅依靠个体,更要加强群体和团体的介入。当一件事由松散的热情变为持续的责任时,也必须要依靠公众体系的制度力量。
本文章从互联网采集,文章摘自于建筑创作订阅,文章版权归建筑创作杂志和作者所有;仅供需要建筑创作订阅的朋友试读,请勿用做它途;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24小时内删除,感谢支持!